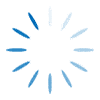待到动身回程时,晨光微明。
齐雪与薛意相偕下楼。薛意负着病体多日,觉察不出周遭异样,齐雪经了穿堂风吹,方捕到客栈的空寂,不禁问道:“掌柜,今日为何这般清静?”
掌柜从算盘上懒懒抬眼,嘴角牵着笑:“你以为只你一人来寻他么?算过命的客官,昨日哭着笑着的,都启程归去了。”
薛意将未结清的银钱轻推过柜台,微微欠身:“这些时日,多承关照我娘子。”
像听得陈年的金珀坠入白瓷盏,光质温润亦传回响清冽,语间风致未损半分。
掌柜这才瞧他个真切。芝兰玉树一般立着,身姿清举,骨重神寒。少许病容未褪,但如傲玥生晕。
那妇人笑意更深,颇不吝啬地慨叹:“今日可算看全了你,也难怪尊夫人衣不解带地照料,竟是万里也无一的男儿!”
这番直誉,令两个素日闺中亲密的人也有些禁受不住。薛意更低着头,别开视线;齐雪悄悄扯他衣袖窃道:“快走罢。”
碧天澄明如洗,是难得的大晴日。
齐雪大抵已将那番挣扎之苦葬在前日,她亲昵地依偎薛意的臂弯,沿路指点风物,闲言絮絮。
他们身形渐小,水滴汇入缓缓溪流,徐徐前行。客栈旁燕青狭深的巷弄,方才悄然转出一道纤影。
那身影静立在煦日所误的阴翳一角,目光穿过长街烟尘,远送着一双壁人。
马车行在小道上,朔风烈烈。
“风这样割人,真不冷么?不如回车中去。”薛意望着紧挨身侧的妻子,眸黯声沉。
“我不……”她连摇头都挨风刀严对,只得将身子靠得更紧:“车里气闷,我就要陪着你。”
薛意方要再劝,眼神骤凛,手臂倏地将她揽紧,同时急挽缰绳。马儿长嘶,车厢猛震,戛然停驻。
“怎么了?”她惊问。
薛意目去遥遥:“前面……倒着一个人。”
齐雪顺他视线望去,一时噤若寒蝉,悬着的心在血肉乱撞。
只见道中蜷着个小小身影,分明是个垂髫女童。道旁散着几户破落农家,想来是附近农户的孩子。
不及细想,她已跃下车奔去。她不敢贸然移动,俯身细察,见地上无血,衣衫齐整,不似车马撞伤,这才稍定心神。
可连唤数声,轻拍面颊,那孩子双目紧阖,软绵绵全无反应,恍若沉眠。
“这……这可怎么办?”齐雪惶然,汲汲四顾却未见其他人,只得求助已安置好马车疾步而来的薛意,声线微颤,“要不留书钉在附近树上,先送她去回春堂?”
薛意敛眉,蹲身探向女孩。他未答话,只轻轻解开女童厚袄,指腹沿其脊背、肩颈几处细细按压。触手之地,竟觉各处皮肉异常僵凝。
他身形蓦地僵住,叁魂七魄如堕阎罗。
“你点穴护我,叫师傅知道了,一道罚你怎么办?”
“师傅岂会知晓?这手功夫是我自个儿琢磨的,独一无二。”
“万一……还是不要为了我冒险……”
“谁说是为你?”那少女不悦,蒙受侮辱似的,“我既立志要成天下无双的高手,岂能没有独门绝技?你乖乖助我验这一手吧!”
每逢切磋败北,便要承二十荆棘鞭刑。皮开肉绽尚可愈合,只是那锥心之痛常追杀到浅浅的梦中,教他难眠。
不知何时起,那总是胜出、压他一头的姑娘,竟自悟一套点穴之道,可使人受刑后暂封痛觉。
后来,他亦将这封脉指悄然习得。此法极难,须在电光火石间寻得二十四处要害,力道重一分则气血壅塞,日久暴毙;轻一分则轻飘飘然,徒劳无功。
这女童年幼经脉未固,被人以此术所制,便陷入假死般的昏厥,弃于荒僻乡道。
见齐雪焦灼神色,薛意深吸一气,翻涌的心绪尽数成灰,唯有沉声道:“我能救她。只是……”他似在斟酌,“娘子可否回避?”
齐雪初时心系女童,便要点头,转念却坚定摇首:“不,我定要在此看着。”
薛意知自己拗不过她,没再坚持。他凝神聚气,但见并指如风,出手似箭,指尖在空中划出淡淡残影,精准落向女童背脊颈侧诸穴。那动作快得超乎目力所及,掀起空中风声悲啸。
最后一指收回刹那,女童惊狂抽气,随即“哇”地放声大哭,声震四野,满是惊惧委屈,却有了一个活娃娃的生机。
哭声立时引来左近寻人的农户。一对布衣夫妇哭喊着,深一脚浅一脚田中奔来:“珠珠!我的珠珠!”
他们初见薛意抱着孩子,面露疑色,待见珠珠哭声渐弱,反伸出小手紧攥薛意衣襟,小脸埋入他怀中,方知遇上恩人。
那妇人拉着丈夫便要下跪,被薛意疾扶住。他只默然将孩子稳稳交还,便携齐雪登车,催马疾离这是非之地。
远处,素白身影雪天一色。灵隐目光遥锁渐行渐远的马车,玉容清冷。
他没有死,他果真是没有死的。
他小心地扶着那女子上车,为她系紧了披风,缱绻旖旎。
而她却仍困在铁壁之内,年少时许下的绝世高手之妄念早已湮灭。
……
他凭什么没有死?
马车上,齐雪握住薛意的手,以自己温软掌心轻轻爱抚摩挲。
“你的手在颤,”她软语,“很冷么?”
薛意的手确在微颤,却非因寒冷。他声音艰涩:“你……没有什么要问的?”
齐雪抬眸,瞳中清濯:“我知道。方才你是在为她解穴,是不是?”
薛意喉结轻动,低应:“嗯。”
齐雪将头轻靠他肩,声若和月温柔:“我不怪你。”
薛意心中失了分寸,讶然看她:“为何?我瞒你良多……”
齐雪语气愈发坚定:“可你这身武功,在擂台上救了钟小姐;识玉之能,使朱大夫觅得至宝;这解穴之术,今日又救了小姑娘。我亲眼所见,皆是你以这些秘密助人。”
她握紧他手,字字清晰如铃:“往事已矣。若因我这点任性,阻碍你行应行之事,我一生难安。”
薛意怔怔望她,胸中滚烫酸胀。
不知何时,雪势转急。漫天冰花旋舞,簌簌而落,顷刻掩去前路。远山近树皆失形貌,化入混沌天地。
前路茫茫,唯见无边无垠的沉郁白皑。二人的低语,连凄厉刻薄、无孔不钻的风霜也听不清了。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